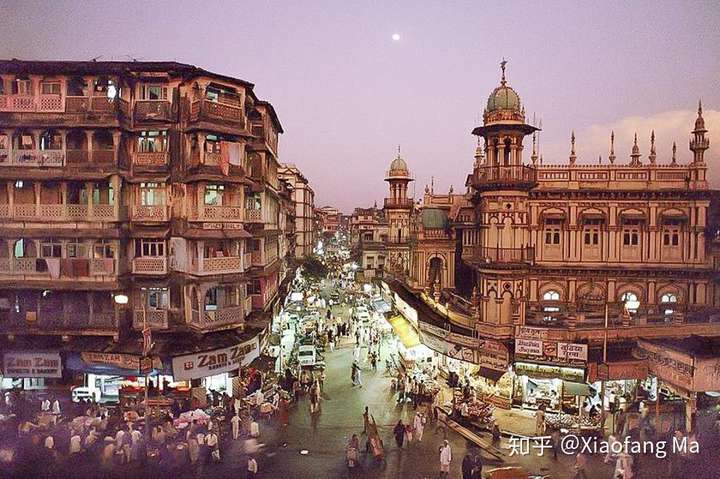【开始本来没想写这篇,因为关于总统候选人的文章太多,让人有点儿视觉疲劳。不过看到文中讲美国中产阶级的破产和经济危机,觉得这倒真是一个全球性现象,所以记一笔。
在美国、在中国,中产阶级都很焦虑:一场大病就让全家破产,孩子上个学就要经济危机。Warren主打的就是这些中产阶级人群。不过,她的政策真要实施起来,能达到预期效果吗?我觉得挺难说。】
In The Ring
by Sheelah Kolhatkar
在二十多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现年69岁的Elizabeth Warren绝对不容被忽视。连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都表示Warren“干得相当不错”。
Warren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专门研究破产法,著作颇丰。她还是哈佛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曾经倡议创立了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自从宣布参加总统候选人竞选后,Warren便一直受到媒体与民众瞩目。在6月的两次民调中,她的支持率已经攀升到第二位,仅次于前副总统拜登。
Warren定位为“务实的中产阶级代言人”,为这一群体最关心的教育、医疗和民主问题带来系统化革新。不过,和竞争对手Bernie Sanders不同,她说自己不打算放弃资本主义。
她说:“我相信市场的力量。”但她希望,通过政府干预,市场能够更好地服务更多的人。

竞选活动演说中,Warren常常以讲述自己的童年故事开场。在她上中学时,父亲得了心脏病。这场突如其来的重病让家里陷入经济危机。
即使病愈后,父亲也无法长久工作,只能打一些零工。她也因之第一次从父母的谈话里听到了“房贷”、“取消赎回权”等陌生的词汇。
一天早上,Warren走进父母卧室,发现床上放着一套母亲参加最重要场合才穿的衣服。当时已经五十岁的母亲从没外出工作过。但那天,她穿上这套衣服,踩着高跟鞋,去本地的西尔斯商场应聘当上了接线员。
虽然接线员只能拿最低工资,但Warren一家的房子终于保住了,算是度过了这场家庭经济危机。
Warren说,她渐渐发现,许多美国家庭都经历过同样的一幕。她也意识到,在她母亲那个年代,即使一个人拿最低工资也足以养活一家三口:可以还房贷、交水电账单、买食物。但现在,一份最低工资的全职工作还不够一位带着孩子的单身妈妈生活。
这段童年历史让Warren在进入学术界后,决定以破产法作为研究重心。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而从80年代早期到中期,美国的个人破产申请数量翻了一倍。Warren和几位同僚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
一般人想来,申请破产的个人肯定都是些不负责任、好吃懒做的人。开展研究前,Warren也如此认为。同事形容她是那种认定“你该为自己欠下的债务负责”的典型美国中西部女孩。
但是,看过1500多份个人破产申请文件后,Warren发现,大部分申请人都曾有中产阶级水平的收入。他们往往是遭遇家庭重大波折后才陷入困境。尝试应对经济危机的行动却给他们带来更多债务。
1989年,Warren和同僚出版了《原谅债务人:美国的破产和消费者信用(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Bankruptcy and Consumer Credit in America)》。她在书中总结道,许多破产者,是一辈子都在勤恳工作的人。
Warren的另一段经历,则让她对中产阶级的处境之难有了更多体会。她和第一任丈夫有一儿一女。在孩子幼时,她必须一边带小孩,一边上班。
回忆那时的生活,她说自己就像骑着摇摇晃晃的自行车在大峡谷上走钢丝,头上还顶着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任务。如果不是阿姨从俄克拉马州搬来帮助照看孩子的话,她很可能会放弃职业生涯。
2003年,Warren出版了《双收入陷阱:为什么中产阶级父母会破产(The Two-Income Trap: Why Middle-Class Mothers & Fathers Are Going Broke)》。她在回忆录中概括这本书的主旨:“最有效的预测一个家庭是否会走向破产的指标,是看他们有没有孩子。”
因为养育孩子的费用激增,但中产阶级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所以人们不得不借债来维持现有生活水平。因此,数百万家庭,哪怕是夫妻双方都有收入的家庭,最终还是来到了经济危机的边缘。
当中产阶级战战兢兢地维护着他们随时就会崩塌的地位时,华尔街的银行和大公司却从中获利颇丰。1995年,美国国会重新审议破产法,邀请Warren加入顾问委员会。在这里,她第一次见识到了大公司游说的力量。
1997年,信用卡发行商游说某些参议员提交了一项不利于个人借债者的新法案。Warren想尽办法阻止这项法案通过,但拖到2005年,它还是通过了,赞成者包括她现在的竞争对手拜登。这让她确信,美国的民主系统受到了金钱力量的极大冲击。
因此,Warren的总统竞选纲领政策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减轻中产阶级负担,例如公立大学学费全免、幼儿照料费用全免;另一是严格管控大公司,例如对大公司征收更多联邦税、拆分大型科技公司和农业公司等等。
在她提出的所有政策中,引发最多议论的,是所谓的“财产税”。她建议,对家庭财富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征收2%的财产税,称为“终极百万富翁税(Ultra-Millionaire Tax)”。
为什么要征收财产税呢?Warren举例说明。一位中学教师和一位家产颇丰的继承人,一年都挣五万美元,但前者银行存款为零,后者则从父母那儿获得了相当于5000万美元价值的“游艇、珠宝和艺术品”。
如果只按收入征税,两人的纳税额是一样的,即使提高所得税税率,也无法改变这不平等的事实。何况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群还有数不清的手段来合理避税。
Warren建议,财产税的征收范围包括“住房、紧密持有的生意、信托财产、退休财产、未成年子女持有的财产、价值在5万美元以上的个人物品”。根据估算,这项政策能在10年之内带来2.75兆美元的收入,可用于免费的托儿所、幼儿园、减免学生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
民调显示,大部分投票者都支持征收财产税,包括半数共和党人。在竞选活动中,每当Warren提到征收财产税时,便会迎来群众的热烈欢呼。
不过,反对财产税的声音也不小。首要的反对者自然是那些有被征税风险的富人。星巴克前总裁Schultz评价Warren的提案“荒谬绝伦”,纽约前市长Bloomberg说征收财产税有违宪法。
此外,财产税怎么实施也是个问题。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Natasha Sarin说,珠宝、古董、艺术品等财产很难估价。如果真的对这些事物征税,一定会诞生帮人们估价并避税的行业。
她说,1990年,全世界有12个国家征收财产税,但现在只剩3个国家这么做。就是因为征收财产税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非常困难。
更有人说,Warren的政策最终会损害经济。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Todd Zywicki说,Warren打算用政府力量干预市场,这样做很可能带来意料不到的后果。比如政府成为某些利益的代言者,损害自由市场。
反对和质疑没有打消Warren支持者的热情,更没有动摇Warren坚持她的政策的决心。
她回应道:“市场机制在激励创新、降低成本、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上是无可比拟的——如果这些市场遵循一定基本规则运作的话”,她说:“没有规则的资本主义就是偷盗。人们说,这个游戏是不正当的,他们说对了。”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