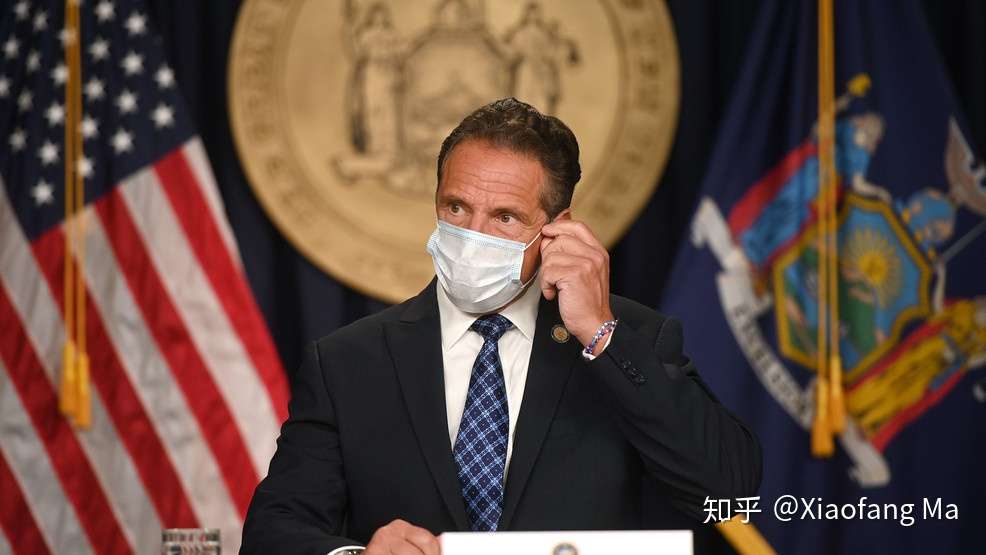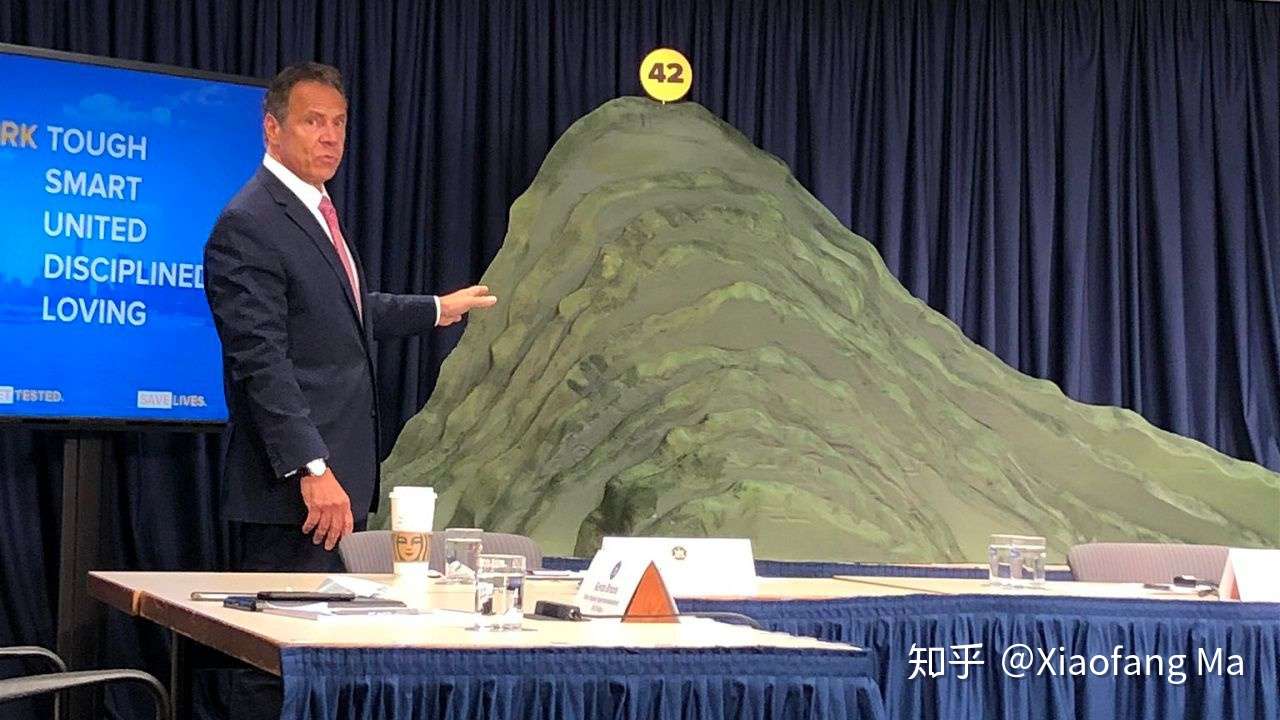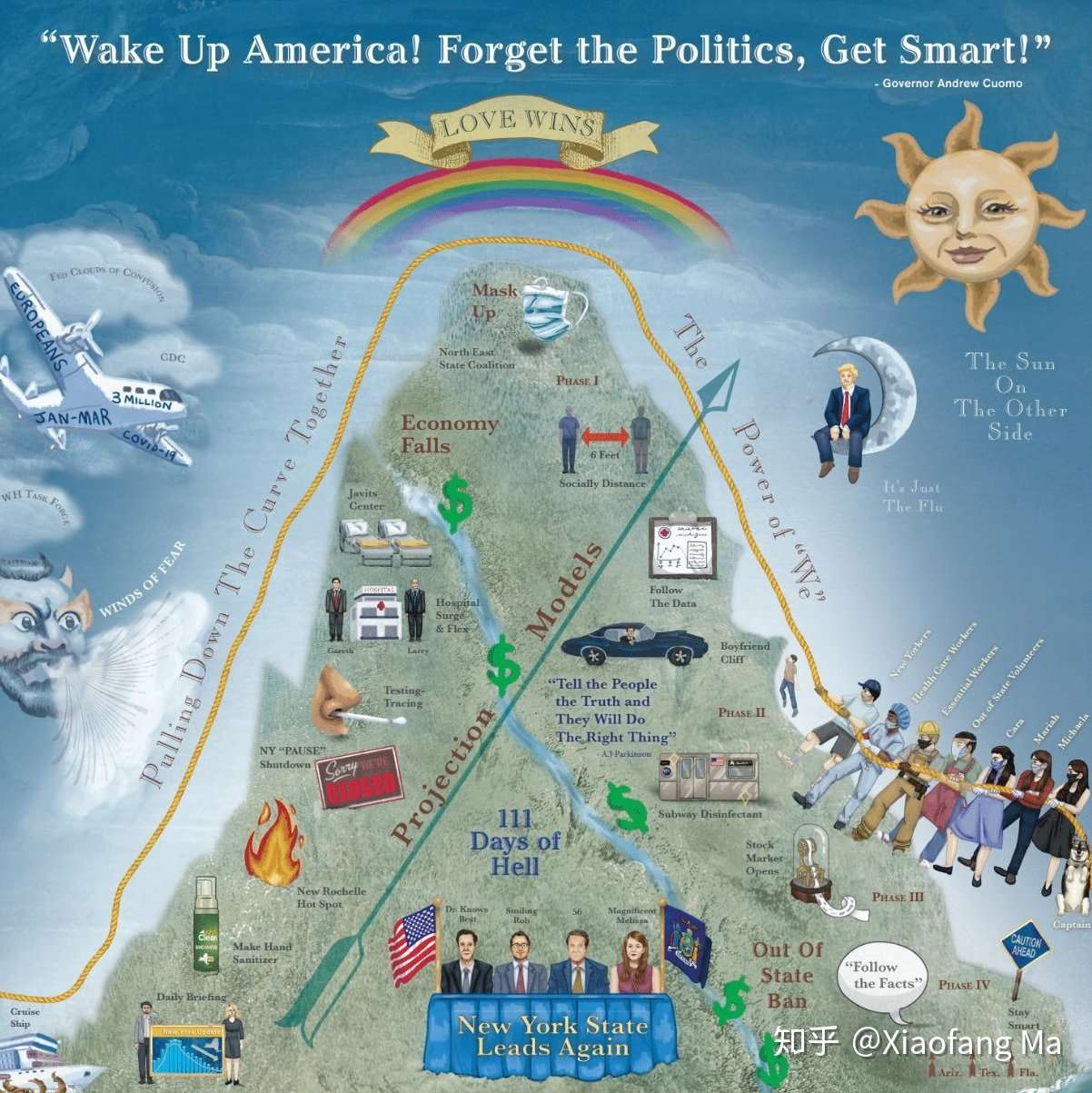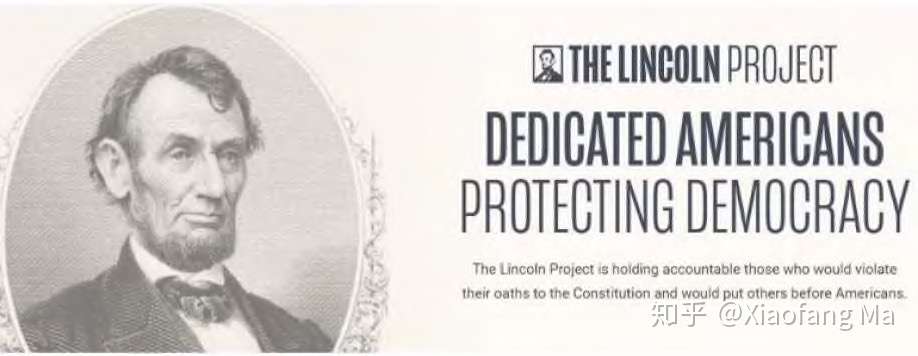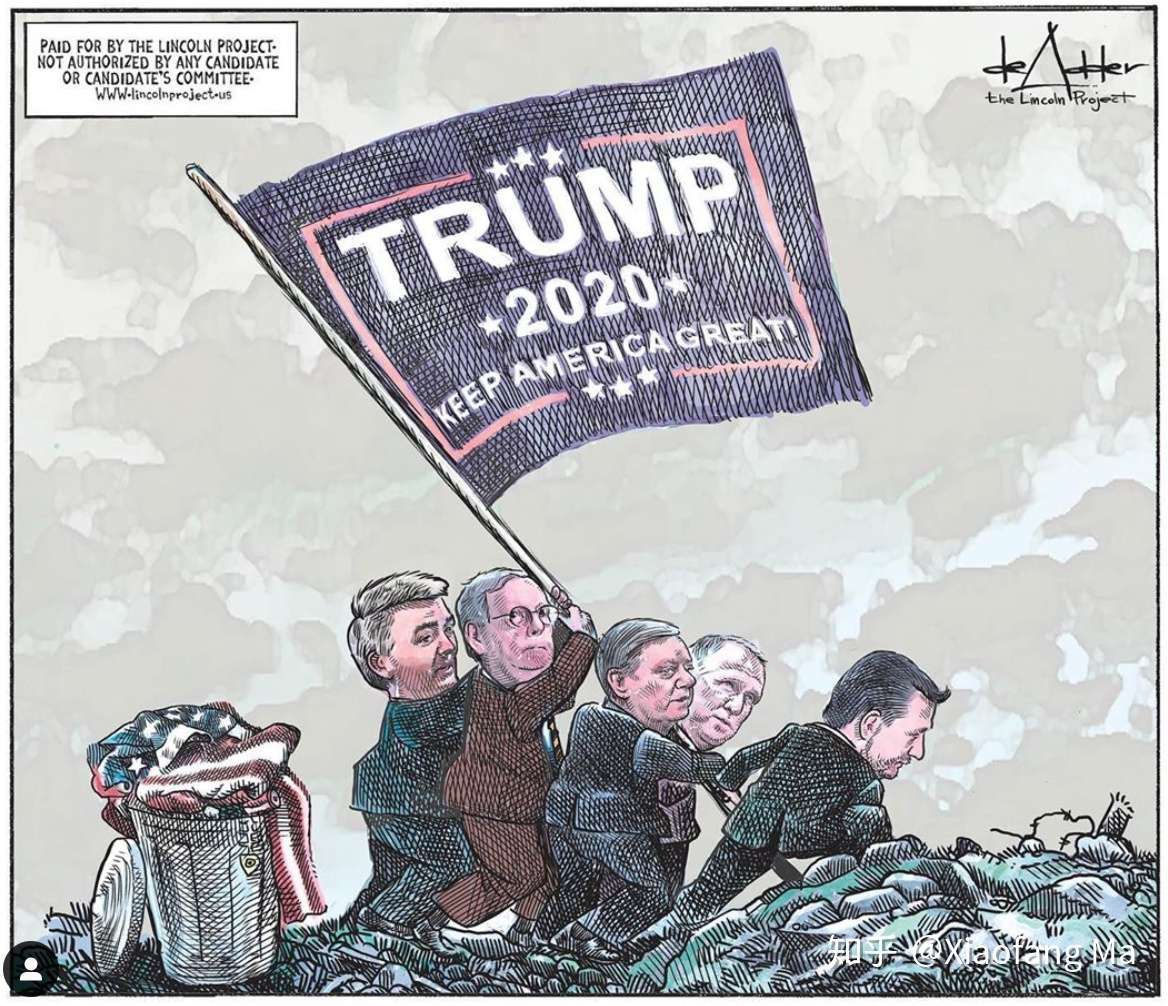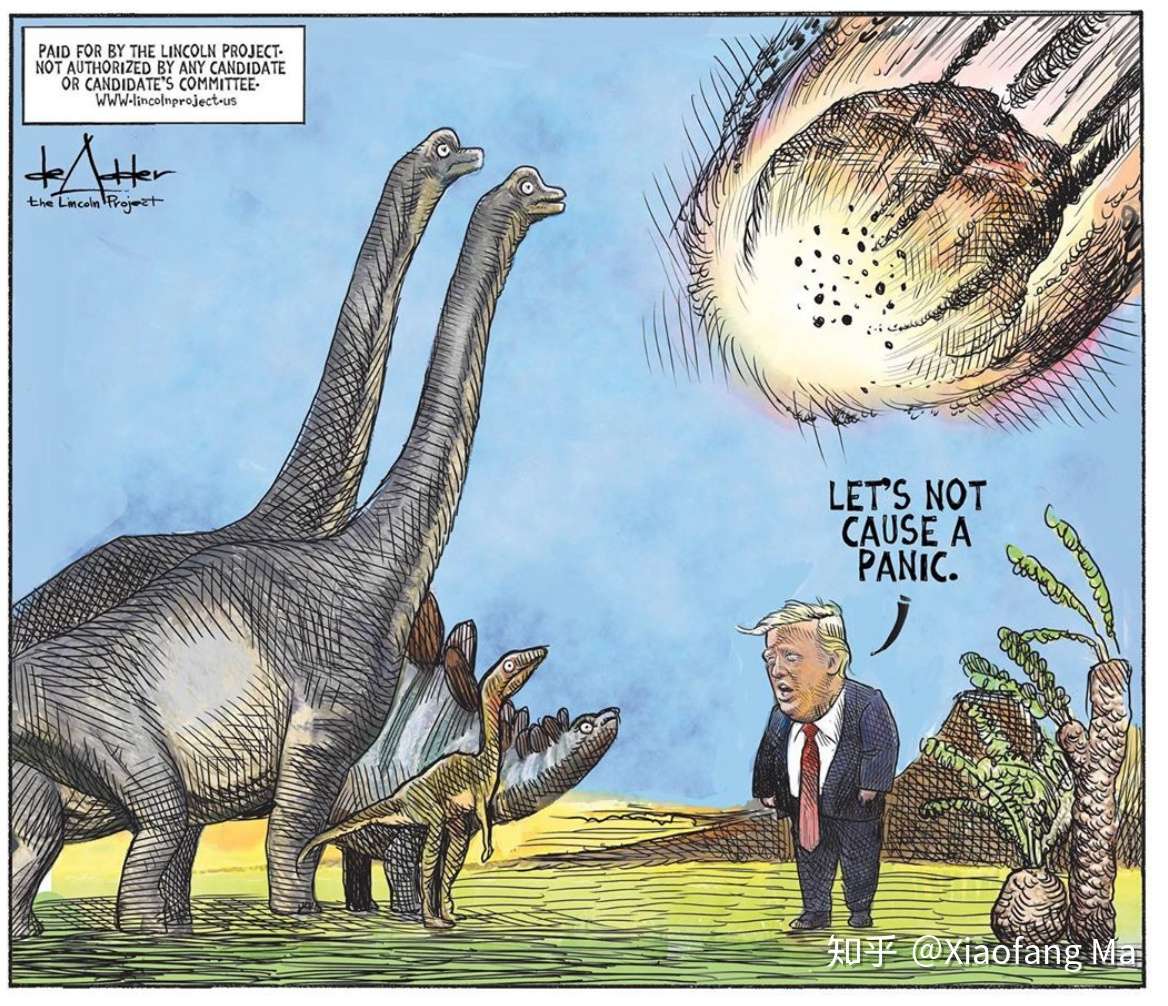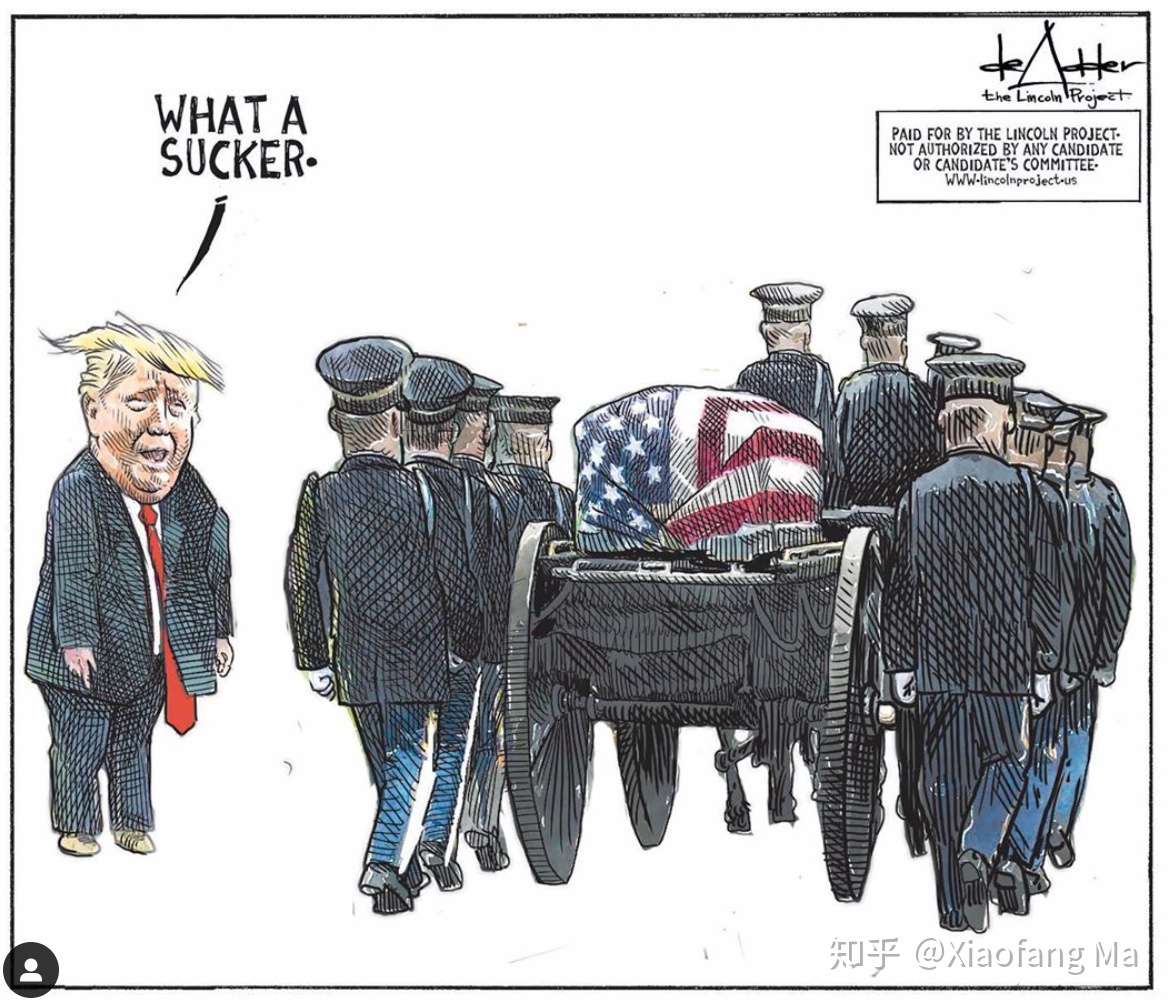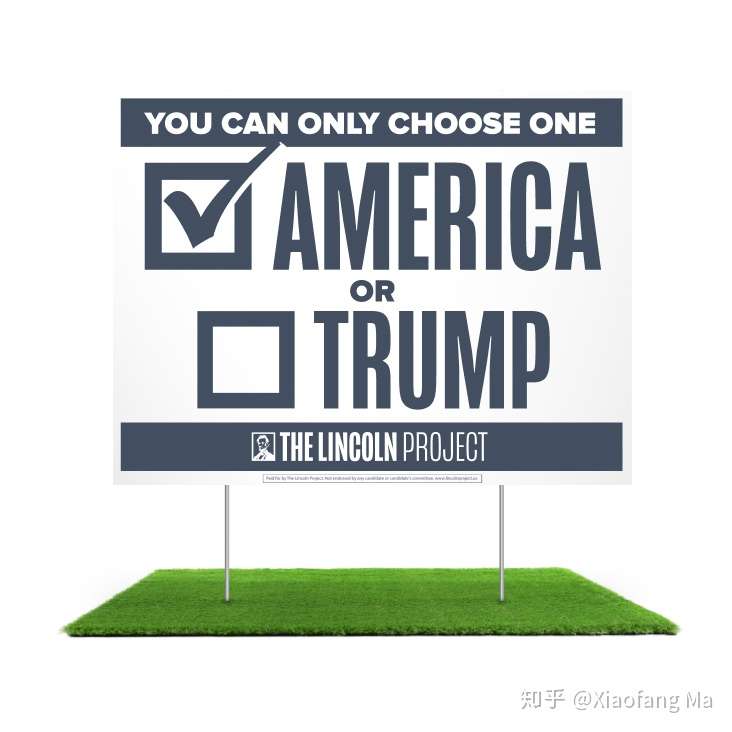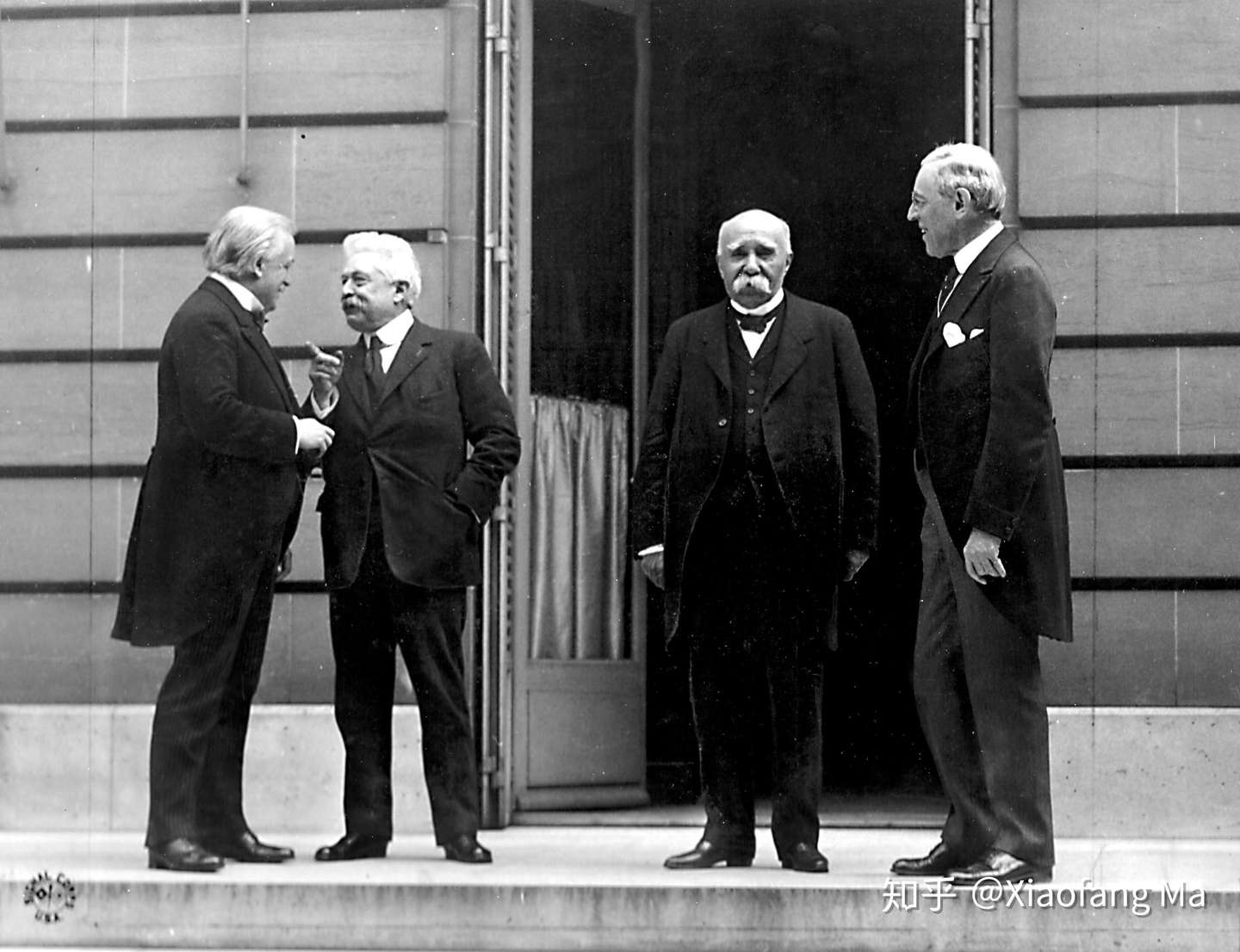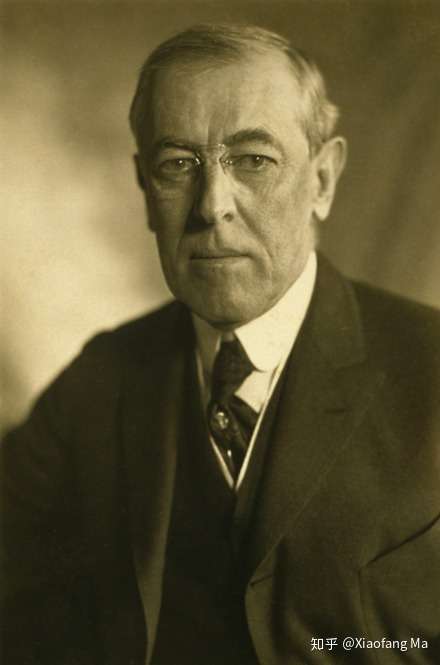Privacy Settings
by
Anna Wiener
前段时间Netflix出了一部纪录片《社交困境(The Social Dilemma)》,讲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公司怎么把用户的数据和隐私转换成商品和钞票,也就是“如果你没花钱买产品,那你就是被卖的产品”。
朋友圈里好几个人推荐这部片子,都说看完后恍然大悟,决定以后再也不给社交媒体当产品了。我倒觉得它没讲出什么新东西,同样的主题光《纽约客》过去几年就刊登过不少相关文章啦。而且相信那几位朋友也不可能逃脱“被产品”的命运——否则首先就应该告别微信朋友圈嘛。
总之,记录片的名字已经坦白道出,这事永远是个两难的困境。大部分人的生活早就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紧密交缠,不用这家的服务,也会用那家的产品。隐私被卖是肯定的,就看卖得多卖得少,卖得你自己认为值不值而已。

除非,有一些真正保护用户隐私的服务——比如这期《纽约客》介绍的Signal——能够成为主流,个人被产品化的命运或许才有可能改观。
Signal是一个端到端加密的通讯应用。通过它发送的讯息,不管是短信、视频、语音还是表情包,都只有发送者和接收者才能看到。就算中途被黑客或者政府部门截获,他们也只能得到一堆毫无意义的字母和数字。
从一个只有极端在意隐私的偏执狂才用的小众通讯工具,Signal在几年时间内就发展成被《华尔街日报》推荐的主流产品。据说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参议院、欧盟委员会都用它。爱德华·斯诺登称赞它是“一种公共基础设施,而且是非常关键的基础设施”。
Signal的CEO莫克西·马林斯派克(Moxie Marlinspike)正是一个极端注重隐私、几近偏执的人。比如说,他拒绝向记者透露过多个人信息,而他所谓的个人信息甚至包括最基本的年龄、出生地和真实姓名。他只愿意说自己80年代初生于格鲁吉亚,莫克西是小时候就有的昵称。
【维基百科上说他的真名是Matthew Rosenfeld,不知是否准确。】

和很多科技天才一样,马林斯派克从小被计算机、密码学和黑客文化吸引。高中毕业后他搬到旧金山,给一些电脑公司打工。那时候正是互联网被炒得最热乎的90年代末期,马林斯派克发现自己崇拜的黑客文化正渐渐被商业化。管它黑客也好,白客也罢(指建设网络安全系统的人),眼里其实都只有一种颜色——绿色(美元的颜色)。
所以,他辞掉工作去全美各地背包游,还迷上了航海(拿到了航海员执照)。与此同时,他靠自己的软件技能做各种项目,既为了维生,也为了兴趣。
2010年,马林斯派克和一位朋友在旧金山湾区成立了一家小公司,研发一系列手机应用。他们开发了两个专门为安卓手机设计的端到端加密通讯应用RedPhone和TextSecure,颇吸引了一些注重隐私安全的用户。不到一年,这家公司就被Twitter收购,马林斯派克被任命为Twitter的产品安全负责人。
但是,他不适应Twitter人事斗争复杂的文化,推崇的端到端加密技术也没被采用,Twitter甚至暂时关闭了RedPhone的服务。2013年初,马林斯派克放弃将近100万美元的股票,离开Twitter,成立了一家非营利组织。
回归自由后,马林斯派克利用RedPhone和TextSecure的开源代码重新开发加密通讯服务。他打算编写一个好用又简洁的加密协议,吸引各大互联网通讯平台主动把它放到自己的产品中。
马林斯派克希望所有网络通讯产品都具备端到端加密功能,所有用户都能借此保护自己的隐私。2014年,Signal出炉了,它既是独立的通讯应用,也是一个可以放进其它通讯产品的加密协议。

2013年底,他结识了通讯软件WhatsApp的创始人之一布莱恩·安克顿(Brian Acton)。WhatsApp被Facebook收购后,他和安克顿花了许多时间,想把Signal加密协议添加到WhatsApp中。
但这可不是Facebook收购WhatsApp的目的。正好相反,扎克伯格想把Facebook的目标客户广告系统结合进WhatsApp。要是WhatsAPP采用端对端加密通讯,那还怎么收集卖给广告商的用户信息呢?最终,安克顿离开了Facebook。
2018年初,马林斯派克和安克顿这两位想推行加密通讯,却先后在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受挫的人联合起来,宣布成立Signal基金会。作为基金会主席,安克顿为它提供了5000万美元无利息贷款。他们希望向所有人展示,即使没有风投和市场的激励,也有可能开发主流科技应用。
作为一家非营利组织,Signal不需要让投资者看到快速回报,也不能被商业公司收购。它采取自愿捐赠的方式提供Signal协议给任何愿意在自己的应用中增添端到端加密服务的公司。Skype和Facebook在它们的私密聊天功能里都用了Signal协议,不过马林斯派克没透露这两家公司捐了多少钱。
马林斯派克说,Signal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普及端到端的加密通讯,而不是将这项技术作为商品出售。作为CEO,他的工资水平在科技界相当一般,少于Facebook员工工资的中位数。

青少年时代的马林斯派克特别喜欢无政府主义理论,直到现在,无政府主义对权威的批评依然影响他至深。大部分科技公司愿意与政府合作,甚至乐于和政府一起开发项目,但马林斯派克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应该有政府和大公司对人们的大规模监视。
2016年,政府曾经要求Signal提供数据。而Signal只能提供某个电话号码创建账户的时间,以及它最后一次链接服务器的时间。它没有在代码中安插所谓的“后门”,所以不可能再看到任何其它内容。
加密通讯严密保护用户隐私,但不是每个人都赞赏它。有人谴责加密通讯给恐怖主义、儿童色情和其它各种犯罪行为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还有人认为它将导致谣言、骚扰、暴力信息的泛滥。
某些国家完全禁止使用端对端加密系统通讯软件,还有一些国家通过法律,要求科技公司必须在它的产品里设计“后门”,便于执法部门有必要时搜集信息。
马林斯派克自然反对以上种种说法。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都应该有一些不想公之于众的事情”。在他看来,法律可以被操纵,哪怕最普通不过的行为或信息,某一天也可能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进一步,他经常举同性婚姻和大麻的使用为例,说人们有时候应该挑战法律,甚至持续参与所谓的“犯罪活动”,迫使法律变革、进步。要开展这样类似于社会实验的行为,隐私是绝对必要的条件。
他说,人们在网络上需要安全的私人领域,就和在生活中需要安全的私人领域一样——私人领域对人的自我认识和成长非常重要,比如说一个孩子在自己的卧室里锁起门,才可以自由探索自己的性别意识。
作为一家不收钱,也不卖隐私的互联网通讯平台,非营利组织Signal在众多硅谷企业中像是个异类,但马林斯派克却觉得这才该是主流常态。
大部分用社交媒体和聊天软件的人都自然而然接受一个前提假设,即他们发送的信息是私人的。他们想要与朋友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照片,而不是Facebook,不是Google,更不是广告商。马林斯派克说,“某种意义上,我觉得Signal的尝试是让互联网回归正常。”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