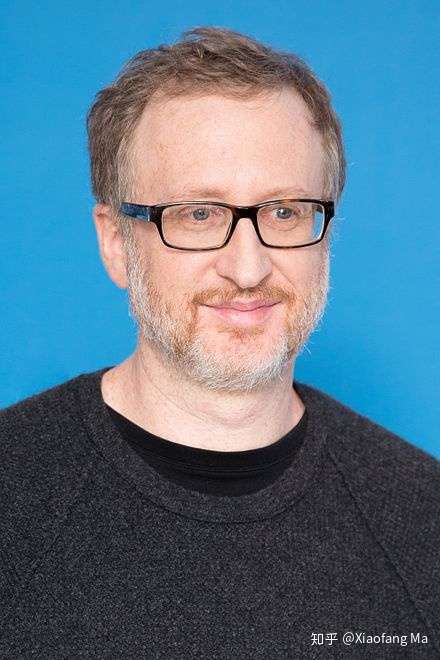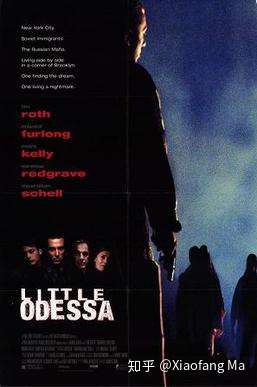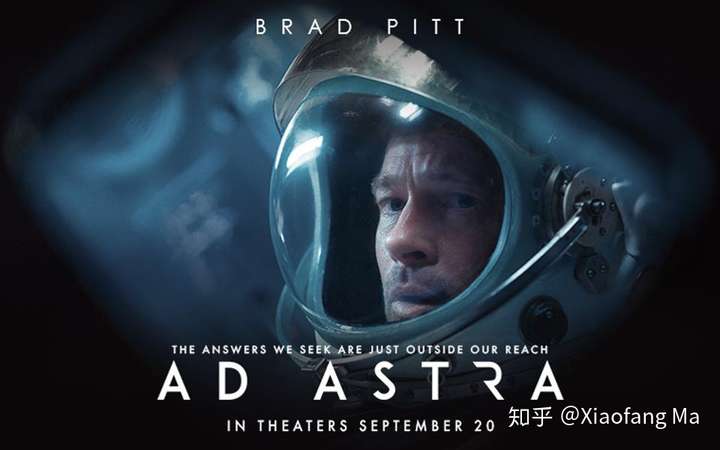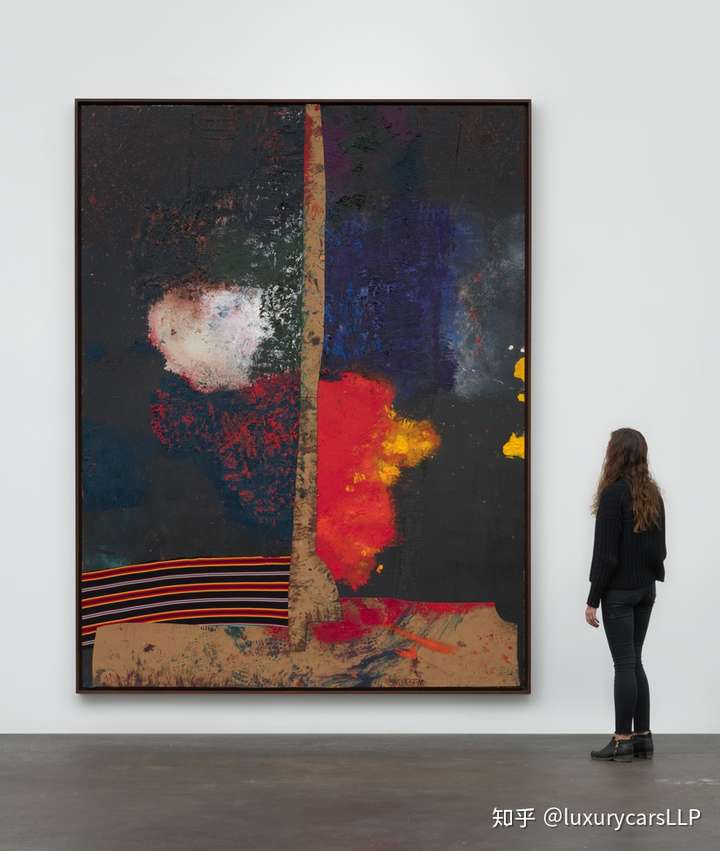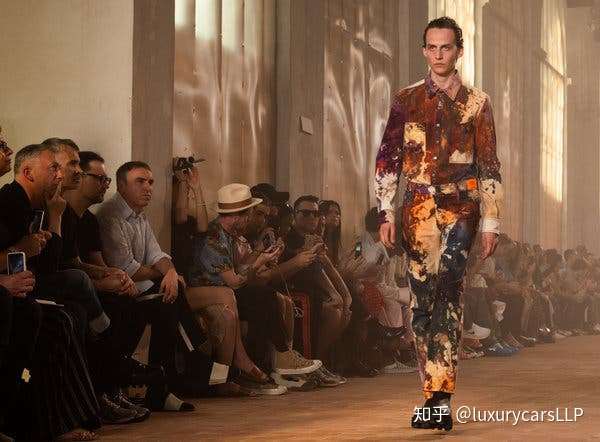Value Meal
by Ted Friend
小时候跟大人去庙里吃素席。满满一桌子菜,盘子叠着盘子:红烧肉、鳝段粉丝、水煮鱼……说是素食,明明闻起来是肉,看起来是肉,吃进嘴里,也像是肉。
细嚼慢咽,才分辨出颤巍巍的五花肉是面筋和蘑菇,弹牙的鳝段用魔芋制成。至于鱼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我怎么也吃不出来。虽然不比真肉美味,但小孩子就喜欢新鲜花样,这顿饭我可是记了好久。
长大后回想起来,才觉出其中的可笑。去庙里诚心虔意吃素,送进嘴中的却是花了大把功夫的仿肉菜,这素吃的未免有点儿滑头滑脑。
没办法呀。对大多数人来说,一桌没有肉的宴席,大概跟不加糖的奶茶似的,喝是可以喝,没准滋味还不错,就是喝完以后少了几分带着罪恶感的满足。所以哪怕是素席,也得想方设法制造点“肉感”。
我们的祖先原本以素食为主。直到250万年前,全球大面积的气候变化影响了许多植物生长,原始人类不得不转而捕捉动物食用。
他们发现,捕猎动物需要的时间比采集植物的时间短,肉类的营养也更丰富。吃肉让人类的大脑更发达,胃部体积相对缩小。对肉类的喜好,从此深深嵌入了我们的基因里。
但生产可食用肉类是最消耗环境资源的人类活动之一。畜养牲畜消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农业用水;全球三分之一的可耕地都用于种植供牲畜食用的植物。过去25年间,人们砍伐了相当于整个南美洲面积的森林,将之改造成养牲畜的草场。
牲畜本身也加剧了碳排放。当牛反刍时,胃里的微生物会产生甲烷。全世界有15亿头牛,它们每年排放的温室气体总和超过了欧盟的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而且,肉类生产能效很低,毕竟牛儿吃草不是为了专门长给你吃的牛排。牛肉的能源转换率——一头牛的肉为人类提供的卡路里相对于牛为了长出这些肉而需要消耗的卡路里之间的比率——只有1%。
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爱吃肉。自1961年以来,全球的肉类生产量增加了400倍。到2050年,预计世界人口将达到100亿,对肉类的需求将会翻倍。如何满足那么多人的需求,同时不对环境造成进一步损害,被称为“2050挑战”。
所以,生产肉类替代品,或者说“人造肉”的企业,过去10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些企业试图用植物材料模仿肉,就像我小时候吃的素席一般。但人的嘴和鼻子都很精明,模仿有一点不到位,就不可能取代真肉的地位。
另一些企业则致力于用动物细胞培养肉。这种肉是真正的肉,但制造成本居高不下。一家硅谷公司目前已经在技术上取得了不少突破,但培养一磅肉依然要花将近4000美元和六个星期的时间。
在这些人造肉企业中,斯坦福大学教授Pat Brown创立的Impossible Foods是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一家。他们生产的人造汉堡肉已经在全美17000家餐馆出售。

今年65岁的Brown是素食主义者,已经40多年没碰过肉了。对他来说,食物仅仅是送进嘴里,用以维持生命的东西。他生产人造肉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而是解决环境问题。
Brown志向很远大:他希望未来五年内抢占牛肉市场两位数的份额,最终消灭这个市场。除了人造肉之外,还要生产人造奶和鱼,在2035年消除全球所有畜牧业和深海捕捞业。

Impossible Foods走的是用植物材料模仿肉的路线,原材料包括大豆蛋白、土豆蛋白、椰子油和葵花籽油等。
但是,一块熟牛肉中含有至少4000种不同的化学分子,其中大约100种产生牛肉特有的芳香和风味,20多种决定它的外观和口感。要让各种植物的大杂烩变得像肉,非得有变魔术的本事不可。
各种尝试后,他们找到了那个魔力要素——血红素(heme)。血红素让Impossible生产的人造汉堡肉在烹煮时保留粉色多汁的外观,并且赋予它如同牛肉一般的风味。
Impossible Foods测试了31种产生血红素的原材料,从烟草到含铁的温泉水。最后,他们发现用基因优化过的酵母加上大豆DNA生产血红素最为方便。在试吃时,一半参与者都不能区分加入血红素的Impossible汉堡肉与真正的牛肉汉堡肉。

与生产同样分量的真肉相比,生产Impossible汉堡肉消耗的水要少87%,需要的土地少96%,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少89%。它的营养与真正的牛肉相当,甚至更好一些。外形、气味和滋味都与真肉几乎别无二致。
从价格上来说,Impossble汉堡肉目前大概比真肉同类产品贵1美元左右。Brown预计到2022年可以将价格拉到与真肉持平。
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汉堡连锁店White Castle已经开始销售用Impossible汉堡肉制作的小型汉堡,销量超出预期的30%。今年8月,连锁快餐店汉堡王也在它旗下7200家店出售用Impossible汉堡肉制作的汉堡王经典汉堡。
据统计,95%购买Impossible汉堡肉的顾客都不是素食主义者。也就是说,这种肉有取代真肉的潜力。

Brown计划,在未来5到10年内,免费向小型创业公司开放人造肉技术。等这些公司获得收入后,再向它们收取专利费。Brown的雄心壮志并不止于自家公司的强大,他真心希望人造肉行业在将来可以完全取代现在的肉类生产。
Brown是个一根筋的学者,眼里只有自己的目标。肉类生产是全球13亿人赖以为生的行业这一点,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和他有一样的想法。
大型肉类生产商目前还不太重视人造肉的威胁,但畜牧业者已经动起来了。美国有12个州在畜牧业组织的游说下立法规定,人造肉食品不能用“肉”和“汉堡”的字样。阿肯色州甚至禁止“蔬食汉堡(veggie burger)”这个短语。
发展中国家也不喜欢Brown消灭畜牧业的想法。津巴布韦学者Lindiwe Majele Sibanda说,牲畜在非洲不仅仅是食物,它们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现金牛”,是人们储蓄财富的手段。Brown的想法太过激进,不够现实。
Brown回应:“把动物作为食物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技术。我们在做的,是挽救地球于环境彻底毁灭之中的最后一搏。”
【在网上搜图的时候,才发现原来Impossible汉堡肉已经在东海岸多个超市有卖。我好像确实在超市里看到过,决定下次买回来试一试。看看它到底是像小时候吃的素席一样,吃个新鲜感而已,还是真能取代肉。若有感想下次来汇报~】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