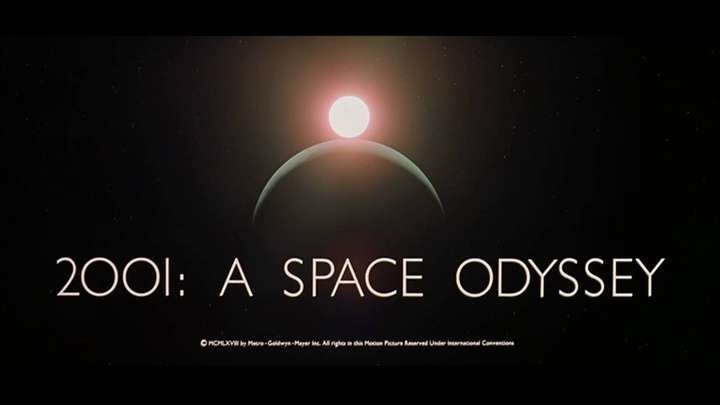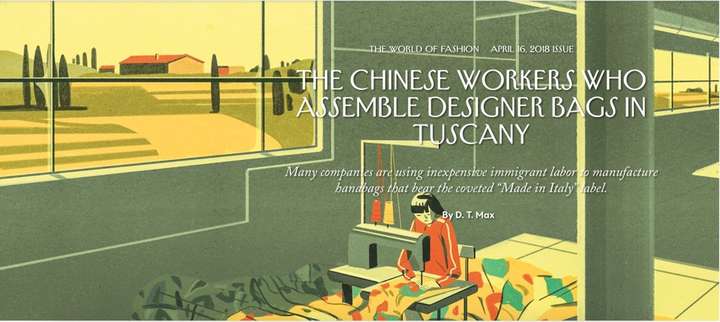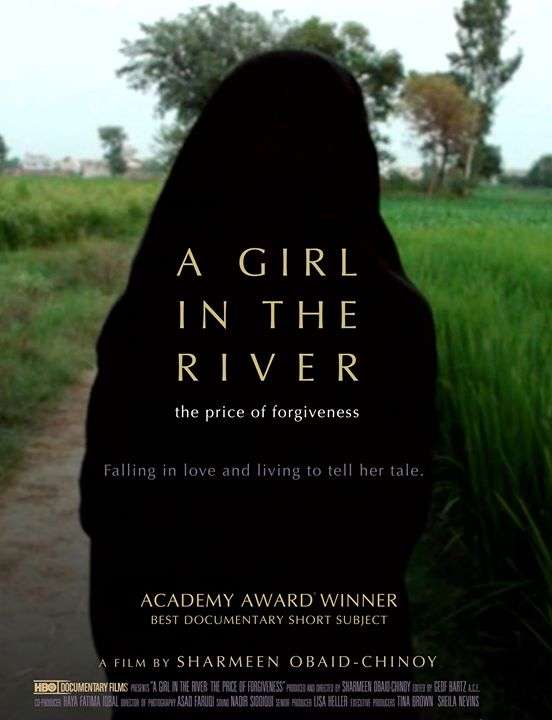每年过年的时候,租个男友或女友回家的新闻已经不新鲜了。不过你大概没听说过租父亲母亲或者丈夫妻子吧?在日本,不管是父母、爱人还是儿女,你都可以租到。
Family Romance是日本一间专门出租家人朋友的公司,有20位正式员工及1200位兼职“演员”。公司生意挺不错,社长Ishii说,光他自己就扮演过近百位女子的丈夫。
为什么有人需要租一位家人呢?失去双亲的男子为完成结婚典礼租一对父母,单身女性为应付亲友租一位男友或丈夫,膝下寂寞的老人租能给自己带来笑声的孙子孙女。你想到或想不到的理由,都是Family Romance这样的公司存在的原因。

Kazushige年过六十,妻子已经去世,独生女儿又因为恋爱问题离家出走。倍感寂寞的他于是向Family Romance租了“妻子”和“女儿”。租赁妻子给他做亡妻最拿手的大阪烧,新的家人陪着他去以前常去的小店吃饭。
渐渐地,三个人都从他们的角色中走了出来。租赁妻子会向他吐槽自己真正的丈夫,租赁女儿则让他理解了年轻人的想法。在租赁妻女的鼓励下,Kazushige最终主动联系上了自己的女儿,摆脱了租赁人生。
租赁家人是Kazushige人生中的插曲,但也有人将之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Reiko是个单亲妈妈,她生下女儿Mana后没多久,就和不靠谱的丈夫离了婚。缺少父爱的女儿总觉得父母分开是自己的原因,在学校她也常因没爸爸遭到同学霸凌。
Mana10岁的时候,Reiko终于找到了Family Romance公司,给她租了一位“父亲”,也就是公司社长Ishii。Ishii每个月来看两次女儿,还会参加学校的家长活动,带Mana去迪斯尼乐园。Mana逐渐变得快乐、开朗起来。现在,Mana已经19岁了,Reiko依然没有告诉她,一直来看她的“父亲”是租来的。
租一位家人听起来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家庭”这个词意味着爱、责任与陪伴,这些东西怎么能用钱买到呢?
但是,对不知情的Mana来说,“父亲”关心她的健康和学习,陪她一起玩乐,如果说他和真实的父亲有什么不同,或许是更亲切、更有耐心。Mana一定感受到了“父亲”的爱。即使对于知情的Reiko来说,Ishii也渐渐成为了她和女儿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有一句大俗话说,爱要用行动表示。光在嘴上说和光在心里想的爱,是无法传达给对方的。如果一个人内心有爱,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表达;而另一个人并不爱,却做出了种种爱的行动。那么对于接受者来说,到底谁能让他感受到爱呢?
对作为“父亲”的Ishii来说,虽然刻意与客户保持一定距离,但多次扮演男友、丈夫、父亲的经历依然让他对自己的真实感情感到困惑:如果你一直在演出好爸爸的角色,怎么知道当你自己有了孩子以后,你为他做的一切是发自内心,而不是又一次演出呢?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以前看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写到娇蕊发现自己真爱上了振保的这一段:
“再拥抱的时候,娇蕊极力紧匝着他,自己又觉羞惭,说:‘没有爱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么?若是没有爱,也能够这样,你一定看不起我。’她把两只手臂勒得更紧些,问道:‘你觉得有点两样么?有一点两样么?’振保道:‘当然两样。’可是他实在分不出。从前的娇蕊是太好的爱匠。”
用钱就能租一份家人的爱,或许还和真实的爱没有“两样”,在单身者越来越多、人情日渐淡漠、老龄化和少子化益发严重的日本,大概是一件很划得来的事吧。
再写一点儿:
日语中的“家族(かぞく)”这个词实际是明治时代才引入的。在那之前,日本人对家庭的概念是“家(いえ)”。和中国人的家不同,日本的“家”是一种代代相传、等级严格的家族制度。有趣的是,“家”并不完全建立在血缘关系上,养子、女婿或忠实的管家、佣人都被承认为“家”的一份子。这大概也是租赁家人在日本感觉不那么突兀的原因吧。
其实,传统家庭成员的许多职责已经在被现代社会消解。比如保姆和月嫂担当了很多过去只属于母亲的职责,社工们代替远离父母的孩子承欢两亲膝下,网络和人工智能在渐渐取代家人的陪伴。租赁人家可以看作是和以上种种类似的服务。
在日本,从2010年开始,单身一人的家庭数量就已经超过了一夫一妻带孩子的标准家庭。据预测,2035年全日本40%左右的家庭都将是一人一户的家庭,标准家庭将只有23%。租赁家人的需求应该会越来越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