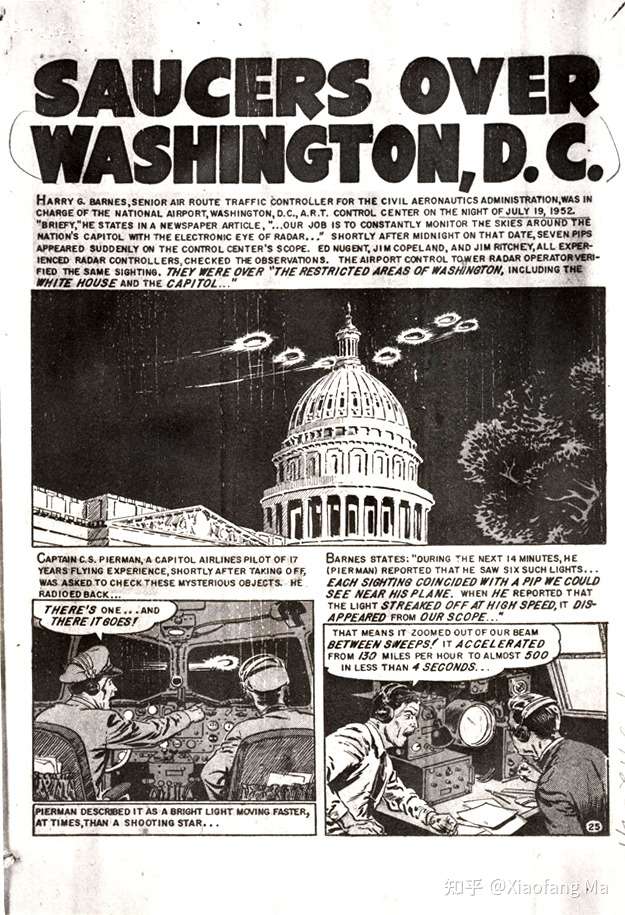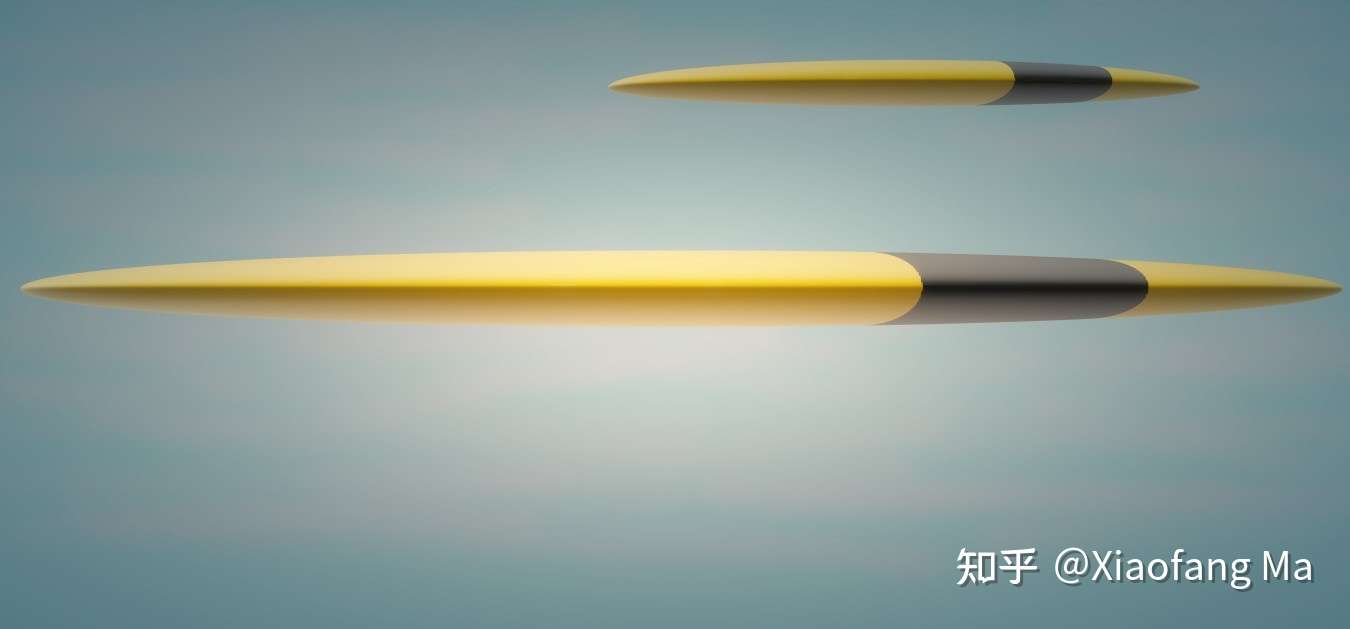It’s Just Too Much
by
Jill Lepore
“Burnout”用中文怎么说,我思索了一会儿。这个词本义是被烧光,引申为过度劳累,身心俱疲,通常翻译成“过劳”或者“倦怠”。
但不管“过劳”还是“倦怠”,听起来总不如“Burnout” 有画面感,简直像一副活生生的蜡炬成灰图。燃尽的蜡烛再也立不起来,只剩一滩不成形状的烛灰,burnout了嘛。
我觉得和burnout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词,是最近流行的“躺平”,都是往地上一摊,再也扶不起来。但躺平似乎是主动选择的行为,而burnout是被动的结果。
硬要给burnout找一个中文翻译,我还是选“倦怠”吧。毕竟很多人平常也没有过劳,但依然感觉自己已经“burnout”。

倦怠是现代人的问题。若问莎士比亚burnout指什么,他肯定只会想到被烧成平地的环球剧场。
据信是在1973年,医生亨伯特·佛罗登博格(Herbert J. Freudenberger)第一次正式用burnout来形容人的精神状态。
佛罗登博格医生积极参与当时兴起的免费诊所(free clinci)运动,为穷人免费看病。1970年,他开了一间免费诊所,白天上班,晚上看诊。当时来免费诊所看病的多数是瘾君子,他们用“burnout”这个词形容自己被毒瘾剥夺一切,除了绝望和沮丧,什么都没剩下。
佛罗登博格医生白天上班10到12个小时,晚上还要去诊所忙到半夜。这么劳碌了一段时间后,他自己似乎也体验到瘾君子说的那种一切都被剥夺,一切都没有意义的感觉。1974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借用“burnout”这个词,以自己和诊所其它员工为例,讲述医疗工作者的职业倦怠现象。
后来,佛罗登博格医生开始专注研究职业倦怠现象。他发现,不仅医疗界,不管哪个行业,不管在哪里,人们普遍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烦和倦怠。
Burnout这个词一下子风行开来。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马斯拉奇(Christina Maslach)做了很多有关职业倦怠的研究。她将职业倦怠定义为一种情绪衰竭、去人性化、缺少个人成就感的现象,经常在做“people work”的人当中产生。
“people work”指帮助别人的职业,比如老师、护士、社会工作者。这些人需要照料其它更脆弱的人,目睹他们的痛苦,会给自己造成极大压力,最后对自己做的事情感到质疑和倦怠。
1981年,马斯拉奇设计了一个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简称MBI),帮助人们测量自己是否已经产生了倦怠的心理。
很快,burnout就超越了“people work”的范畴,同样在1981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大公司的管理阶层普遍出现了职业倦怠现象。
Burnout的应用范围随之越来越广,不管什么职业都能用上。1990年,一位学者将荷马史诗翻译成英文,其中阿喀琉斯说自己不希望被人们看作是“a worthless, burnt-out coward(一个没有价值,厌倦一切的懦夫)”。给古希腊人都用上了“burnout”,可见这个词有多流行。
越多人谈论burnout,就有越多人觉得自己burnout。据说冥想静修可以改善职业倦怠的症状,但就连专长冥想静修的宗教人士也无法从burnout中逃脱。不少宗教媒体纷纷刊文,提醒牧师们注意职业倦怠。
burnout渐渐不再只限于对职业的倦怠。网络时代来临,大家开始讨论“数字倦怠(digital burnout)”,还有对婚姻的倦怠,对养孩子的倦怠,对兴趣爱好的倦怠,对周围一切的倦怠。
现代人的生活围着工作转,也习惯了用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一切。在英文语境里,一样东西不能好好运转,就说它不“work(工作)”了。婚姻work起来,为人父母的角色work起来,一切都要work起来。把所有事情都当工作,自然对所有事情都倦怠。
最后,连佛罗登博格医生都说,他对burnout这个词感到了burnout。马斯拉奇则在今年三月份的《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希望大家谨慎使用burnout这个词。

调查显示,全世界每五个职业人中就有三个说自己在经历职业倦怠。2020年美国的一项研究更是说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三个人burn out。年轻的一代被形容为burnout的一代。甚至连地球也在burnout——我们是一群burnout的人正在burn out地球。这究竟怎么啦?
如果人人都burnout,什么事都burnout,那要么人生本就是一场或长或短的burnout的过程(这也太悲哀了),要么就是在比个人层面更高的地方出了问题。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在他的书《倦怠社会(The Burnout Society )》中将现代人普遍的倦怠症状归结于社会形态的改变。
他说,当代社会是一个浅薄的只看成就的社会(achievement society),大家都在追求成就。这个社会过分强调积极,见不得一点负面因素,满世界高光正能量。
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最后演变成一场对自己的战争。最终结果不是达到理想的成就,却是被理想烧光。
有意思的是,最初使用burnout这个词的瘾君子们,大都是越战退伍兵。他们忍受着战争创伤后遗症,用毒品麻醉自己,最后对一切都不再感兴趣。今天感到倦怠的人或许同样忍受着战争创伤对自己的战争,对人生的战争。
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记得自己小时候,最常听老师说的话之一就是“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还有“人往高处走”,还有“坚持就会实现梦想”。
听着这些话长大,再听着某些成功者奉这些话为人生格言而终于成功的传说,我们开始一场人生的战争。最后的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战争败兵,点燃的火光照亮少数传说中的成功者,自己只落得burnout的结局。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