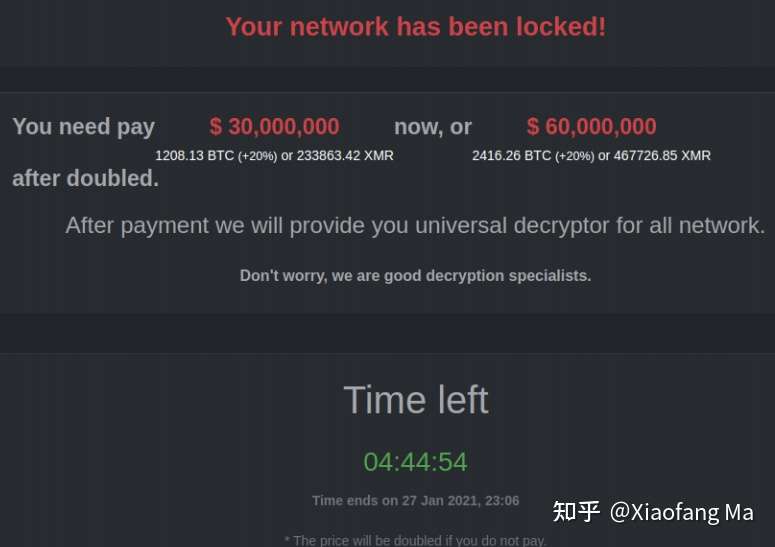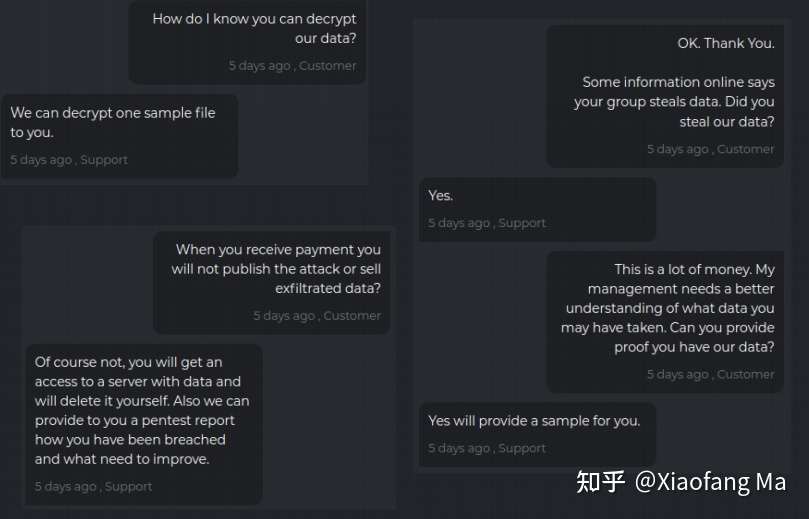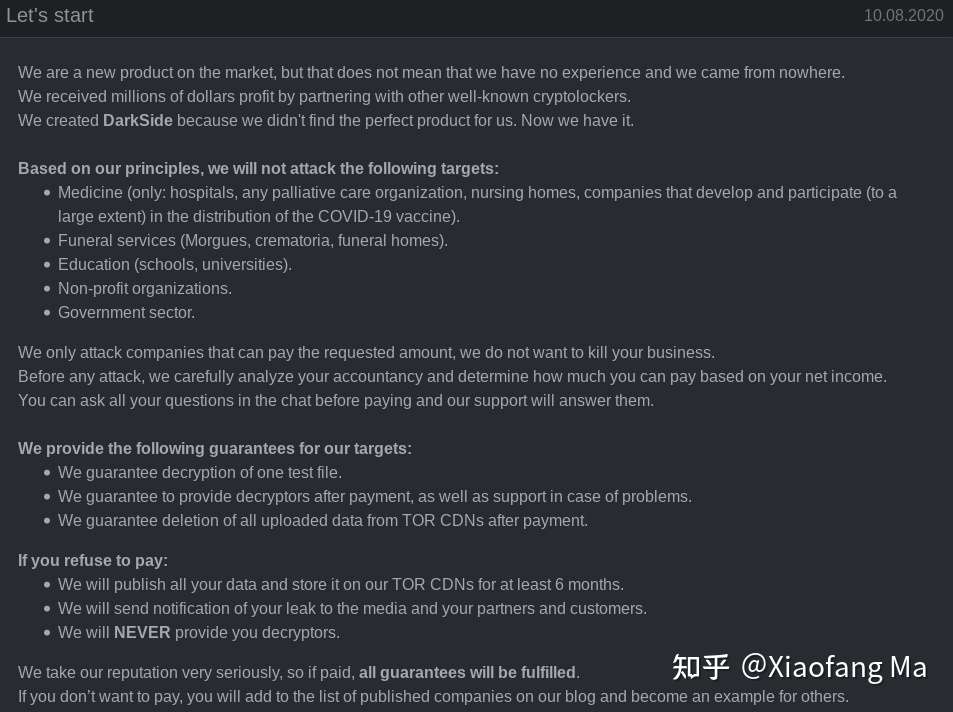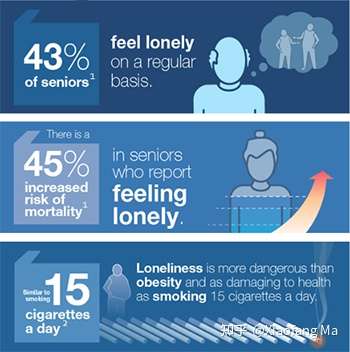特朗普在位时,我常抱怨媒体上关于他的新闻太多。但不可否认,他是挺能吸引注意力的。他当总统那会儿,《纽约客》上和政治相关(通常也和他相关)的文章我几乎都会看;现在他走了,这类文章就常常被我归入太长不看的行列。
这期这篇《Undecided Voter》是个例外,文章很长,但我还是看完了。原因之一是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算我们的老朋友啦;原因之二是上周CNN的安德森库珀专门就这篇文章采访了欧逸文,我正好瞄到那次采访,于是好奇文中到底讲了些什么。
文章讲的是一个人——民主党资深议员,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乔·曼钦三世(Joe Manchin III)。曼钦和拜登的名字都是“乔(Joe)”,有些媒体说,除了坐在白宫里的那个Joe之外,曼钦要算全华盛顿最有权势的Joe了。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现在,美国参议院里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的席位正好是一半对一半。所以民主党政府想通过一项议案,自己党内的任何一票都绝对不能放弃。
而曼钦是立场最保守的民主党人,民主党提出的议案常因为他的一张反对票夭折。
在拜登当上总统的这头几个月里,已经有好几项议案因为曼钦的反对被否:
- 曼钦反对拜登提名尼尔拉·坦顿担任美国预算办公室主任(他不喜欢坦顿在twitter发表的强烈反共和党的言论);
- 曼钦反对拜登政府将公司税提高到28%(他认为25%更合适);
- 曼钦还以一己之力让议会降低了Covid纾困法案中的失业补贴福利;
- 今年六月,曼钦作出了他的职业生涯中最保守的一个选择。他决定反对民主党的选举改革法案“For the People Act”(他认为这个法案缺少共和党人支持);
- 同时,他还拒绝修正冗长辩论战术(filibuster)规则——要不是差他这一票,民主党本可以通过这项议案的。
【冗长辩论战术(filibuster):指的是在议会中议员发表马拉松式的冗长演讲和辩论,拖延议会进程,迫使与自己对立的一方作出让步。】

曼钦为什么要和自己的党派对着干?他说,这是因为他坚定相信两党必须合作,民主党想要干成什么事,必须得到共和党的支持。这个信念与美国目前两党对立的趋势完全背道而驰。
然而,两党越分裂,曼钦就越觉得需要让两党协力共事。他曾经发誓,不管双方政治主张或个人风格有多大冲突,他都永远不会在选举活动中攻击任何一位在任的参议员。
特朗普时期,曼钦曾给好几个特朗普任命的官员投过赞成票。为了不与党内人起冲突,他的策略是保证自己的票不是决定性的那一票。他这种做法让进步派的民主党人很生气,却又拿他没办法。
如此一来,曼钦当然和他的党内同僚们矛盾重重。矛盾的根本在于他们对共和党的看法。对许多进步派民主党议员来说,共和党是无药可救的敌人;但对曼钦来说,很多共和党议员是他的邻居和朋友。
曼钦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美国最穷的州之一。今年四月的全美人口普查显示,西弗吉尼亚州的人口过去十年间下降了3%。人口下降意味着联邦拨款减少,政治力量减弱。
高贫困率和对政府的不信任让西弗吉尼亚州的人们越来越保守。过去六届总统选举中,这个州选的都是共和党总统。从2014年开始,共和党完全控制了州议会。

曼钦是民主党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唯一代表。从2000年开始,除了曼钦,这个州的所有国会代表都是共和党人,他这一根独苗能留下来殊为不易。
曼钦出身于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天生拥有意大利人的热情天性。从政前,他从事销售工作,善于和人打交道。据说,每次他和你谈话,都能让你觉得你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关心的人。
著名政治科学家理查德·费诺(Richard Fenno)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家乡风格(Home Style)》,他发现美国人通常对国会没什么好感,却积极支持本地的国会议员。他认为,成功的政治家能树立一种家乡风格,从而获得家乡人民的信任。
曼钦就把握住了西弗吉尼亚州的家乡风格。有人评论说,在西弗吉尼亚州,所有事情都和政治相关,除了政治本身以外——在这里政治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正好是曼钦最擅长的。
2020年总统大选,拜登在西弗吉尼亚州差了特朗普39个百分点;而曼钦连续赢了六次参议员选举。就算进步派民主党员不喜欢他,他依然是唯一能帮助他们抵挡共和党势力进一步扩大的人选。

拜登和曼钦这两个“Joe”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是70多岁的白人天主教徒,都骄傲于自己的工薪家庭出身,都曾是橄榄球运动员,都很亲民。他俩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共同点——比起坚持某种政治理念来说,他们都更看重能够通过协商和妥协达成的具体事务。
拜登和他的顾问们正在尽全力争取曼钦的支持。奥巴马当政的八年间,他只给曼钦打过三次电话;拜登上台这几个月以来,已经至少和曼钦会面/通话六七次了。
不论进步派的民主党人怎么看,曼钦所持的相对保守的立场是以西弗吉尼亚州的人民为代表的,数百万美国人的立场。他们是那些不赞同特朗普,但也不赞同AOC的美国人,是那些感觉自己正被民主党渐渐抛弃的乡村美国人。
【AOC:民主党进步派代表,众议员议员亚历山卓·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昵称。】
公众号:NotesofTheNewYor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