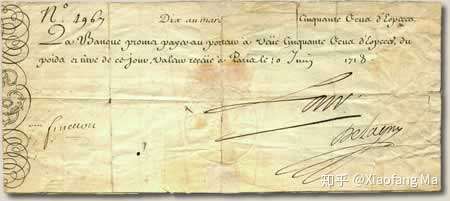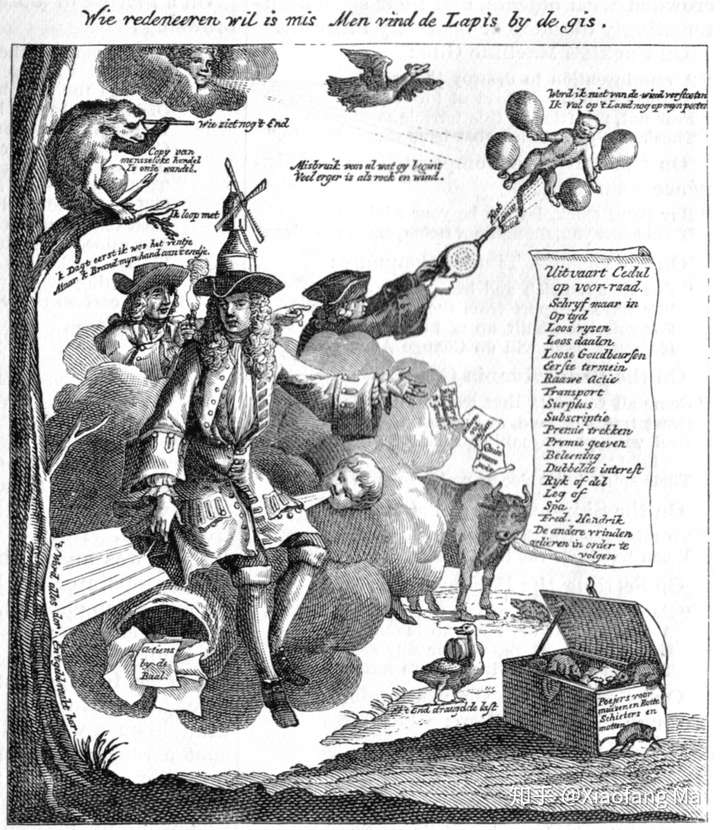Trouble in Paradise
by Andrew Marantz
这篇文章,让我想到了《黑镜》第五季第二集:一边是伦敦郊外田野中,情绪崩溃的网约车司机绑架乘客,只求与互联网大佬通话;另一边是美国西部渺无人烟的山野中,该大佬正在玻璃别墅里打坐修行。

站在时代潮头的互联网科技大佬,与打坐修行避世隐居,怎么看怎么不搭。但是,如今的硅谷精英们,确实在通过类似形式,寻求心灵慰藉。
在《黑镜》里,互联网公司Smithereens的社交APP占据了人们的全部注意力。男主角在开车时分心看了一眼APP推送,结果导致未婚妻车祸身亡。
现实生活,大抵没有剧中故事那么极端。但是,有人刷着社交网络上朋友的完美生活而怅然若失;也有人为在网上打造自己完美生活的形象而计较不已。许多人埋头于网络,却迷失于现实世界。互联网科技,说是让生活更美好,有时却让生活更不美好。
因此,曾令人仰慕的硅谷各大科技公司在近年来已渐渐脱却光环。侵犯隐私、散布谣言、干扰注意力、降低生活质量……它们身上背负的罪名越来越多。
长久以来,硅谷精英给人的印象,是近乎傲慢的洋洋自得。现在,他们开始感到羞愧。有人说:“在硅谷,一种意识正在觉醒。人们认识到,他们的成功并不一定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Tristan Harris是觉醒者中一员。2013年,他是Google的一名项目经理,负责Gmail。他发现,开会时,同事们最关注的是“怎样让这东西更吸引人”,而不是“怎样合乎伦理地来设置这种可能会操控人类大脑的东西”。

Harris觉得良心不安,他把自己的思考写下来做成PPT,一时间在互联网上疯传。他在PPT中写道:“我很担心,因为我们的行为,而让全世界人类的注意力无法集中。我们应担起巨大责任,改变这一现象。”
当任何一个人,一家公司,或一个创意威胁到Google的商业模式,Google的解决之道很简单——买下来!在Harris发出这份PPT几个月后,Google就任命他为公司的第一位“设计伦理专家(disign ethicist)”,研究如何解决类似问题。
但是,Harris的研究结果很少实现。周围人觉得他的建议太复杂、太困难,往往与商业底线相悖。两年后,他从Google辞职,开始自己单干。
Harris创建了一个名叫Time Well Spent的组织。“time well spent (好好利用的时间)”既是组织名称,也是宣传口号。他发表TED演讲,接受媒体采访,致力于引起人们关注。

Time Well Spent的宣传是有成效的。人们对科技公司的不满情绪日益累积,像Harris这样的硅谷觉醒者也越来越多。
Apple和Google相继发布帮助用户管理注意力的手机软件。扎克伯格在他的Facebook日志上写道:“2018年,我们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让人们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都是‘time well spent’”。
虽然看到了一些成果,但Harris认为,这只是迈向成功的小小一步。他将Time Well Spent重组为非营利组织Center for Human Technology (人类科技中心),并且推出了新口号:human downgrading (人类能力衰退)。
Harris相信,就像能源公司造就了环境危机一样,科技公司引发了人类的注意力危机。新科技让人类的社会能力衰退了。我们必须重新找回那种能力。
许多硅谷精英认同Harris的想法。他们或许没有勇气像他一样辞职,却也找到了另一种途径来反思。那就是去伊萨兰(Esalen)。
伊萨兰是什么?
据说,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对伊萨兰一无所知,另一种则声称了解它的一切。
伊萨兰是什么?
那儿的一位工作人员形容:“伊萨兰是流散之地。是人类集体黑暗中点亮的一盏明灯。是一个箭头,指引着我们成为完人的最优路径。”
现在,伊萨兰也是硅谷精英们安抚自我良心的一所精神疗养院。
其实伊萨兰没那么神秘,它实实在在存在,离旧金山不过3小时车程。它全名伊萨兰学院(Esalen Institute),成立于1962年,注册为非盈利组织。

伊萨兰坐落在加州1号公路和太平洋之间,沿大苏尔海岸的27英亩土地上。它的中央大草坪就像一块闪亮的翡翠,被包裹在海岸峭壁中。
在这块草坪上,阿道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作者)和蒂莫西·利里(心理学家,嬉皮士教主)曾经教授过“药物神秘体验”的课堂;弗里兹·珀尔斯(心理学家,完形治疗创始人)开办过“完形治疗研讨会”。
琼尼·米歇尔(著名歌手)曾在这儿高歌一曲“Get Together”;若威香卡(印度教大师)则给乔治·哈里森(披头士成员)上了一堂西塔琴课。

伊萨兰创始人Dick Price和Michael Murphy都是斯坦福毕业生,但都将内在精神追求作为毕生事业。(当然他们也都颇具家产,无忧生活。)他们形容伊萨兰为“新思想实验室”。
今年已经88岁的Murphy说:“我们的目的,过去是,也将一直是,让人走出传承的正统信念,去发现真相。这些真相可能有关自身心理,可能有关不朽精神,也可能有关社会伦理行为。”
当然,在现实中,伊萨兰主要还是有钱人的避世之地。一个周末晚上的住宿需要420美元,而且你得带上自己的睡袋。房间高级一些,价格就暴涨到了3000美元左右。

钱,难不倒硅谷精英。过去,这里是嬉皮士的天堂乐园。现在,硅谷精英同样在这里寻找天堂。
伊萨兰有草坪、海洋、露天温泉,但最多的是各种身心灵活动。不过,你从它网站上或媒体报道中看到的活动,只是其冰山一角。伊萨兰的许多活动从不对外公开。
比如说在1980年代,伊萨兰就组织过美国和苏联宇航员,以及CIA和KGB特工交流的活动。1989年,叶利钦曾在伊萨兰的赞助下来访美国。
现在,伊萨兰帮助硅谷精英通过静思和讨论,寻找精神追求和人生真谛。在这儿,一刻不得闲的高管被要求关上手机,不能谈论任何与工作有关的话题。他们打坐、健行、讨论、写日志、全身心沉浸在自然中。

这些活动有用吗?至少,许多参与者表示,他们开始学习正视自我,潜心思考。
某位目前很流行的某手机APP的创始人说,过去,他衡量成功的标志是用户在他的手机APP上花了多少时间。现在,他开始考虑,或许应该将“用户少花了多少时间在手机APP上”作为指标。
就在最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几个国家的Instagram用户发现这个APP有了显著变化。在他们发表的照片下,没有了“赞”这个按钮。Instagram希望,人们将注意力放在他们分享的内容上,而不是计较得到多少个赞。
当然,光让科技公司高管打坐静思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这能否让他们开启智慧。否则,打坐可能只会成为麻醉自我的工具。
也有人批评说,光靠内部自我觉醒不够,只有外部压力,如政府、股东和媒体,才能改变公司行为。比如说,要改革金融系统或能源行业,最有效的手段是制定政策,法庭起诉,利益激励,而不是让一群高管打坐写日志。
不过,和传统行业不同的一点是,许多科技公司高管真正相信他们在创造一个美好世界。当创新没能带来理想中的乌托邦时,这些高管感受到了更大的心理冲击。
这些被时代潮流裹挟着一刻不停的硅谷人,或许需要Harris这样的人来说出心中的话,也需要伊萨兰这样一个地方来反观内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