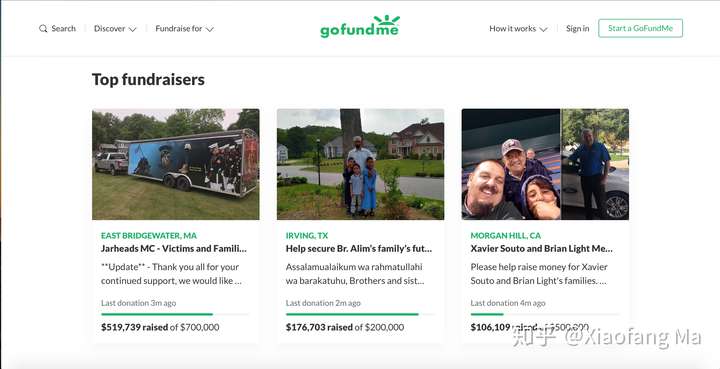The Voice
by Rebecca Mead
米开朗琪罗雕塑的《大卫》应该算是美男子标杆了吧?静态的大卫已经迷倒了无数人,如果是动态的呢?如果这个大卫还有一副高亢动人的嗓音呢? 现在就有这么一位古典歌手,被赞为“活生生的米开朗琪罗的大卫”。

看真人版大卫之前,先来了解一些背景知识,学一个新单词:countertenor。维基百科上翻译为假声男高音,也就是用假声唱法可以让自己的声音达到女声音域的男声。
由于没有录音,假声男高音的历史资料模糊不清。总的来说,由于过去女性不能登台表演,歌曲的高音部分便由男孩或会唱假声的男人担当。一位17世纪早期的威尼斯游客就曾记录,自己碰到了一位“有全世界最甜美嗓音”的男歌手。
进入17、18世纪,假声男高音被阉人歌手(Castrati)所取代。有歌唱潜力的男孩们被阉割,以保证能永远保持高亢清亮的声音。
但是,阉割不一定有效。据说在18世纪上半叶,每年光在意大利就有4000名男孩被阉割,但只有少数几位有幸一直拥有好声音。
到19世纪,这股阉割男孩的风气渐渐没落,人们转而欣赏更为正常的男高音和男中音。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著名歌手Alfred Deller又重新燃起了音乐爱好者对超高男声的喜爱。之后,假声男高音歌手开始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Jakub Józef Orliński是一位年轻的波兰假声男高音歌手。他一头小卷发、湛蓝的眼睛、方正的下巴,外加健美的运动员身材。粉丝们公认,假如米开朗琪罗雕塑的大卫有一天活了过来,他的长相和声音就应该和Orliński一样。

1990年出生的Orliński生长于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祖父母一辈都是建筑师,父亲是平面设计师,母亲是儿童艺术家。Orliński很小就进入华沙的格里高利男声合唱团,接触到了古典宗教音乐。
16岁时,Orliński和其他几位合唱团成员组织了一个小团队。有一天,他们开始练习文艺复兴吟唱歌曲中带有高音的部分,需要两名假声男高音配合。Orliński和他的一名朋友是这群人中最年轻的两个,于是他开始唱起了假声男高音。
除了合唱,Orliński其实没有太多音乐背景,连乐谱都不太会读,主要靠耳朵来学习音乐。但18岁时,他还是被华沙最有名的音乐学院萧邦音乐大学录取。大学毕业后,他又前往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进修。

2017年的某一天,Orliński刚在法国艾克斯音乐节完成了首场演出,就接到了音乐节组织者的一个电话。原来一家电台第二天有一场直播节目,原定在节目中表演的合唱团临时不能去,组织者便来找他救场。
因为是电台节目,Orliński没刮胡子,穿着皱巴巴的衬衫和大口袋短裤,踢着球鞋就去了现场。到了那儿才发现,原来节目还会在Facebook上视频直播。可他已经没时间再去整装,只好以这幅看上去像没睡醒的形象高歌一曲。
这场表演的视频在YouTube上被浏览了350万次。Orliński邋遢的外表反而更加凸显了他清晰感性的声音。自那时起的两年来,他成为了一小群假声男高音明星歌手中的一员,参与了一系列巴洛克音乐的演唱和制作。
【巴洛克音乐是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古典主义音乐形成前所流行的音乐类型,大约从1600年到1750年之间。它的特点是极尽奢华,加入大量装饰性音符,旋律精致。代表作曲家包括巴赫、维瓦尔第、亨德尔等。】
Orliński的硕士论文主题就是巴洛克装饰风格,他完全掌握巴洛克艺术的规矩,知道怎样有创造性地在演唱中表现出这种风格。有评论家把他的吟唱比作“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
虽然唱的大部分是17、18世纪的歌曲,但Orliński却是不折不扣的现代90后。他是霹雳舞高手,曾是某个获奖霹雳舞团的成员。虽然舞蹈生涯已经为歌唱让位,但在他发布的Youtube视频上,你还是能看到Orliński在华沙的楼房屋顶上倒立和旋转的场景。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Orliński喜爱社交媒体,他在Instagram上po自己在欧洲各地旅拍的照片,通过Facebook和粉丝们直接交流。因此,他拥有了一大批比通常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们年轻得多的观众。
18世纪时,演唱亨德尔或维瓦尔第创作的巴洛克歌曲的歌手是当时的音乐明星。在Orliński看来,自己要欢快地继承前辈们曾经的明星地位,而不应表现得像个虔诚的博物馆策展人。
他说:“我看待巴洛克音乐就像看待流行音乐一样,只不过巴洛克音乐流行在当年那个时代罢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Justin Timberlake。表演让我感到新鲜和有趣,我想从中获得乐趣。我可不想变成那种僵硬古板的样子——‘我要唱经典音乐,所以必须严肃’。”